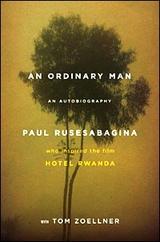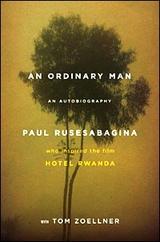

1994年4月6日,卢安达这个国家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,短短一百天之内有八十万人丧生。一天八千人,每分钟五个人!在这个血腥发指的三个多月,有一名豪华饭店的经理在他工作的饭店匿藏了一千两百六十八个人,保全了他们的性命。这段经历拍成了电影《卢安达饭店》,尔后电影的真实主角,也就是饭店经理Paul Rusesabagina 现身说法,写了《我辈凡人》(An Ordinary Man) 这本自传,记述在那场屠杀梦餍中,他是如何与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军人周旋,想尽办法劝阻他们闯进饭店搜索。
到底是什么原因,造成这般腥风血雨?
贾德•戴蒙在《大崩坏》认为人口过剩,土地短缺,是造成种族屠杀的「一个重要因素」(391页)。另外一个戴蒙没有讨论的重要因素是种族仇恨。Paul Rusesabagina在这本自传交待了来龙去脉。
卢安达主要分为胡图与图西两个种族,前者务农,皮肤较黑,轮廓较扁平;后者畜牧,皮肤较白,轮廓较明显。然而,这些外表差异,不足以构成两个不同种族的根据,主因很可可能是早期白人探险家的错误区别,然后以讹传讹,被殖民者与政客操弄的结果。
第一个踏足中非大陆的英籍探险家John Hanning Speke在现今的卢安达看见这两个外表与生活方式不同的群体,就武断地假设以放牧维生的图西族出身高贵,而种田的胡图则出身卑微。
比利时管辖卢安达的时候,为了分化族群,易于统治,就利用这种传说「见缝插针」,选了皮肤较白的图西族作为统治阶级,帮执民政府掌控管理。比利时的科学家甚至声称,图西族的鼻子比胡图族长2.5毫米,并且于1933年发了「身份证」,特别标示种族,并且在社会上鼓吹图西族较优越的理论。
但是到了1950年代,欧洲殖民势力日渐式微,独立运动正席卷非洲大陆,比利时见大势已去,于是在卢安达举行大选,胡图族赢得九成席次,并且于1962年 7月1日宣布独立。很多图西族人流亡到邻国,人数多达二十五万,其中些激烈份子,开始组织游击队,在卢安达边境发动突击行动。因为这些人多于夜间出没,于是被胡图人称为「蟑螂」,日后成了对整个图西族的蔑视称呼。这些流亡在外的图西人念念不忘要重返家园,于1990年果真攻入卢安达境内。当时执政的哈比瑞玛那总统 (Juvénal Habyarimana) 一方面迫于外界压力与情势与判军和谈,一方面为了巩固政权,与他的人马私下发起两个行动,造成日后的大屠杀。
1993年8月,卢安达出现一个新的广播电台,简称RTLM,播方轻快活泼的非洲音乐,接下来是广播节目,日后又增加扣应,上天下地、荤素不忌,什么都可以谈。相较其他的八股节目,RTLM远为生动有趣,吸引很多听众。游击队进入卢安达境内不到三天,政府宣布叛军已经大举入侵,在各地发起战争。其实是政府的军队受命夜间在各地鸣枪制造假象。
同时,RTLM的节目越来越激烈火爆,声称国家安全受到「内部」的威胁,完全归咎于图西人,并且在扣应节目上争辩如何让这些图西人吃吃苦头。人民并不知道,这个号称是民间电台的幕后老板,其实就是哈比瑞玛那总统,成立这个电台的目的就是要煽动人民的愤怒,并且把目标指向图西族。
1993年11月,有大批卡车开进首都,上面装载了987箱的廉价开山刀,收取这批货运的正是RTLM电台。其实,1993至1994年之间,卢安达引进了将近五十万把开山刀,没有人公开质问,要这么多的开山刀作何用途。
1994年4月,当哈比瑞玛那总统搭乘的飞机被炮弹击中身亡,正好成了引爆点,历史上最迅速的大屠杀于焉一发不可收拾。
Paul Rusesabagina亲眼看间他四周的胡图邻居,这些平常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,个个穿起军服,拿着军方发的开山刀,闯进那些他们认为是图西族的家中,带着滴血的开山刀出来。
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狂魔?Paul Rusesabagina答案是:言语的威力。
固然,欧洲殖民政府挑拨微不足道的族群差异,难辞其咎。固然,谬误的族群优越感――我们比对方聪明美丽――与自卑感――我们比对方丑恶愚蠢――在作祟。当然,广播电台鼓动人民在自己的社区消灭图西人,是造成暴力的主因。当然,联合国的懦弱与西方国家视而不见的态度,要负起责任。
但是,Paul Rusesabagina认为,这一切总归起来,是因为言语这个火力最强大的武器被我们滥用――挑拨的言语,仇恨的言语,推拖的言语….
汉娜・鄂兰 (Hannah Arendt) 在法庭上看见执行屠杀犹太人命令的纳粹军官艾希曼 (Adolf Eichmann) ,无法置信是眼前这个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人,造成这场生灵浩劫。因此,她写出「邪恶的平庸无奇」(banality of evil) 这个词句。后来,她在文章里解释,「行为骇人,但行为者――至少,现在受审的这一个――是个非常平凡、普通的人,不是什么妖魔鬼怪。」
拜科技所赐,言语与文字在今天极其普遍通行,也因此变得极为廉价。今天任何人坐在电脑萤幕前,都可以畅所欲言,放在无远弗届的网路世界,随意流窜。躲在电脑后面,我们不必顾忌用语是否恰当,礼仪是否得体,我们想要说什么,就可以说什么。我相信,很多恶毒的文字出自平时看来儒雅文静的人;很多激烈的文字出自平时看来温文寡言的人。
这些形诸于笔墨的言语,威力不亚于说出口的言语。在这个网路书写盛行的年代,我们何其需要发挥更高的自制与反省的力量。若是任仇恨与愤怒恣意横行,敲键盘的手难保不会变成拿开山刀的手。在卢安达,拿开山刀的不只是军人而已。
 |
|
 |
|
 |
|
 转寄
转寄